|
因为“文革”风暴的突然降临,导致只写了三场戏的《焦裕禄》,是笔耕一生而屡遭劫难却始终牵挂着人民的作家赵树理留给我们的一首最凄美的绝唱。打开那段尘封的历史,没有谁不会为作家对人民特别是农民的那份赤诚所感动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经过了小说《卖烟叶》横遭批判和上党梆子《十里店》被领导处处掣肘、一些人往死里折腾之后,有着几十年耕耘生涯的赵树理,的确心灰意冷了,决心按照省委的安排,在晋城县委副书记的任上,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至于创作嘛,暂不去考虑它了。
可是,当他看了县剧团移植的焦作市豫剧团《焦裕禄》的演出之后,却认为:有戏,也能感人;但有些唱词不太适合上党梆子演唱,场与场的衔接也不那么顺畅。于是,他拿了剧本回县委招待所去了,要好好读一下。
他先是默默地看,接着又像修改《十里店》那样,将一张旧报纸折成十六折,边敲边看边唱,敲着敲着,终于停下来了。
“不行!这本子不能使!”
随即把一件黄大衣一披,夹起剧本出门了。
他要去剧团找团长李近义。
“近义!弄坏了!把事情弄复杂了!”他敲开团长的门,带着一股春夜的寒气说。
这把封了火、烫了脚,准备睡觉的李近义吓了一跳。
“怎么啦赵老师?”
他目光烔烔地盯着黑暗中的赵树理,神情有些紧张地把他拉进屋里来。
执着的人民作家,直到这时也没有从剧本中解脱出来。他把剧本往李近义面前一放,仍然激动地说:
“全国有两千多个县,当过县委书记的人成千上万。焦裕禄之所以能名留青史,受人敬仰,是他在生命最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斗内涝、治盐碱的感天动地的事迹;绝不是他怎样与病魔作斗争、怎样悲壮地离开人世!”
“我的天!赵老师,你是在说剧本呀!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吓死我了。”李近义如释重负地说。
“我原想着小修小改一下就行啦哩,谁知道,焦作的剧本把重点放在焦裕禄之死上了。”赵树理点着烟,美美吸了一口说,“这怎么行呢?看来内容上有改动之必要,内容一动,当然就得重新布局了。你看是不是把事情弄复杂化了!近义呀!《十里店》把我累了个半死,难道再让兰考的风沙折腾一番?”
“赵老师,你看情况。要觉得太费劲的话,不改它吧。我看现在的本子也能演。”李近义知道一些《十里店》的情况,表示同情地说。
“你这个思想不对!咱们作为文艺工作者,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老百姓,不能糊弄老百姓!现在眼看着老戏快不行了,群众没戏看咋成?”赵树理批评说。然后拖了把椅子,在火边坐下了。他把两只冰凉的手捂在火筒上暖着,陷入深思。显然,他在心里权衡如何对待《焦裕禄》。
“不能这样将就!咱抹了桌子重调菜呀!”不知过了多久,他往起一站,声调和语气都十分坚定地说,“我先看资料,要是有必要的话,恐怕还得去一趟兰考!”
“啊?去兰考?现在?”
“对呀!不去实地感受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近义,现在是春天,正是兰考一年一度风沙迷漫的时节。不抓紧去,就很难与风沙碰上面了。”
“哦呀!赵老师,据说兰考的风沙不是一般的风沙!你六十多的人了……”李近义担心得说不下去了。
“嘿嘿,没事。近义,人常说老人是风地里的一盏灯。我还不到那个时候哩……”
当天黑夜。当招待所五六排平房的灯光渐次熄掉以后,赵树理仍然在灯下仔细阅读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他瞪着熬惯夜的双眼,一行一行地看着,用红笔画着,作着只有他自己能懂得的眉批、旁批。
经过几天几夜的苦读,赵树理不光熟读了那篇通讯,而且把报章杂志上有关焦裕禄的通讯报道、回忆文章、评论随笔……差不多都找来精读了,剩下来的,就是身临其境,去感同身受了。因为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文字上,无法在心里形成具体的印象。几天后,在征得县委的同意以后,赵树理披了那件黄大衣,与县委办派的一位小通讯员,乘着一辆北京吉普上路了。
他们的采访活动,先从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开始,分别采访了在焦裕禄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守在床前的两级党组织的负责同志,第三天,赵树理一行在开封地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陪同下,才赶到兰考县。
沿途看到的场景,那是多么让人揪心啊!一片一片的黄沙,一座一座连绵起伏的小沙丘和尚没有治理好的星罗棋布的盐碱窝,使得赵树理心如刀割。这位农民的儿子,此时此刻,他把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当成了自己的父老乡亲。他坐在小车上,设想着这“三害”如何疯狂地折磨着兰考人民,和兰考人民怎样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挣扎,他的鼻子一酸,一股辛酸涌上心头……
在县委会,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接待了赵树理一行。
由于常在乡下跑,显得很粗糙的大脸盘上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放射着智慧光芒的副书记,不仅向远道而来的著名作家讲述了焦裕禄同志的苦寒身世和生前的工作、生活情况,还把他们领进焦裕禄同志生前的办公室参观。
在这里,赵树理看到窗下一张三斗办公桌,后墙根摆着一个茶几、两个简易沙发,书柜后是用板凳支起来的木板床,床上铺着洁白的床单,叠着一床薄薄的棉被———虽然他的家就在附近的县委家属院里,但因为他常常工作到深夜,这里便成了他的临时卧室。赵树理仔细地看着这一些,突然,那把在长篇通讯里出现过的、为了缓解肝痛而被焦裕禄同志顶了一个大窟窿的藤椅,映入了人民作家的眼帘。
好像苦苦寻觅了多年突然在家乡遇到了亲人一样,赵树理瞪着那把藤椅惊呆了。随后,在众目睽睽中,他一步一步地走近藤椅,无限深情地抚摸着它和那个拳头大小的洞。那情景,仿佛焦裕禄同志还坐在这里,还在病痛的折磨中孜孜不倦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着……
按照来访的安排,第二天,赵树理一行要到张庄去。那里的沙害最厉害,也是焦裕禄同志生前去得最多的地方。据兰考陪同人员说,现在那里虽然栽下了一排排泡桐树,但因尚小,那趁风而来的滚滚黄沙远没有被封住。为此建议不去。但执著的人民作家却坚持要去那黄沙遍野的不毛之地,亲身感受一下风沙的厉害和治沙的艰难。
春天是风的天下。走的时候,县里为每人预备了防风眼镜和带护领的帽子。还告诉他们,如果遇上大风或者流沙,一定要迅速撤离低洼处。“有这么厉害吗?那里会有生命危险吗?”赵树理在心里说。他觉得兰考县委办的同志有点危言耸听了。
但是,当他们进入张庄地界以后,愤怒的狂风搅得天昏地暗,根本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扑面而来的黄沙打在人的脸上,只觉得火辣辣地疼。要不是戴着风镜,大概两只眼睛会被风沙填满吧?通讯员和司机一人一条胳膊搀着赵树理,在沙海中跋涉。他们无法说话。因为一张嘴就是一嘴沙子。当风小的时候,领路的同志向他们介绍了焦书记生前率领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经过几个月的奔波、方圆五千里的跋涉,终于使县委掌握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
在兰考五天时间,赵树理沿着焦裕禄生前的足迹,遍访了“治沙典范”张庄、“治涝模范”赵朵楼、“改造老碱窝先锋”秦寨和“泡桐大王”老韩陵。虽然是走马观花式的,但通过实地看、听群众访,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焦裕禄精神,看到了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最贫穷落后的县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兰考回来,为了集中精力创作上党梆子《焦裕禄》,赵树理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一天的活动场所,除了宿舍,就是餐厅。那时候的招待所条件相当简陋,室内没有卫生间。他去方便,来回总是小跑步。隔三差五,从餐厅带一双竹筷子回来,用作鼓箭,边写边敲边唱。有时写着写着,遇到难题了,他把灯一关,靠在沙发上,陷入长时间的思考中……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在“文革”那场暴风雨到来的前夜,赵树理写出了《焦裕禄》的一至三场。不仅写得戏味很浓,文采飞扬,而且他把布景、灯光、音乐以及唱腔板式,都标得清清楚楚。李近义是这样评价这三场戏的:“没想到戏开到火车站,把火车也戏曲化了……第三场下大雨那一段写得更精彩。屋里屋外,房上房下,处处有戏,使焦裕禄所处的环境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感到他既是群众中的普通人,又是群众的领路人。”(刘长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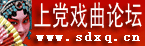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4/5/14 11:54:45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14/5/14 11:54:45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4/5/15 8:43:39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14/5/15 8:43:39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4/5/16 15:57:06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14/5/16 15:57:06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4/5/20 13:33:34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14/5/20 13:33:34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