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李鲁平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戏曲艺术家的命运当然是与戏曲艺术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的三十多年,也是戏曲艺术挣扎、生存、发展的三十多年,对于长篇小说《楚生》所写的楚剧艺术家“楚生”来说,也是命运多舛的三十多年。
作品借助记者坚持不舍的采访,在刻画楚剧艺术家楚生的成长和成熟中,勾画了楚剧艺术的历史和发展。十九世纪中叶,黄陂、孝感人沿着黄孝河源源不断进入汉口定居、谋生、繁衍,这是汉口历史上重要的一支移民队伍,他们也是今天很多武汉人的祖先。黄孝人不仅带来了汉口的繁荣和黄陂街、花楼街的兴盛,也带来了黄孝花鼓戏。以黄孝花鼓戏为种子,楚剧在黄陂街生根发芽,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成为武汉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戏剧艺术。小说从楚剧的源头写到楚剧的衰落,其间,楚剧艺术界的大师、名作、事件等等穿插其中,从一个层面再现了楚剧艺术的历史。可以说,关于楚剧艺术的历史可能有丰富或系统的总结,但以文学的方式来叙述楚剧的历史,把楚剧的艺术史与武汉的城市史结合在一起,把楚剧的发展与楚剧艺术家的个人命运融合在一起,《楚生》是第一次,它使得我们第一次通过一个楚剧艺术家的个人命运去感知一个城市的历史和一个剧种的兴衰。
《楚生》也堪称一部用武汉方言叙述的、深入武汉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长篇小说。自近代开埠以来,无论是对这座城市的社会历史的叙述,还是对这座城市的精神历史的叙述,在文学上都是缺乏文本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基本没有文学上的观照。书写武汉这座城市一个很大的难度便是,作家既要了解这座城市,又要能叙述这座城市。这种了解不是知识层面的“知道”“知晓”“明白”,而是需要作家的骨子里流淌着这座城市的精神血液;这种叙述当然也应该是植根于武汉城市文化的思维习惯和表达习惯。但当代武汉城市题材小说创作的大多数作家都是改革开放前后进入武汉这座城市的,他们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或多或少存在隔膜,这种隔膜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是很难弥合的。但鲍红志有着独特的优势,他与小说中的“楚生”一样,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记忆和情感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街弄里巷和万种风情的感受和领悟,不是“了解”和“知道”,而是来自“基因”“遗传”和“本能”。在《楚生》长达30万字的叙述中,作者选择了基本用武汉市民语言来完成对城市日常生活的讲述,如“撮白”“乌漆抹黑”“蛮坯”“堀倒”“撇脱”“惊嚷鬼叫”“糟鄙”“邋瓜”“捞摸”“翻呛”……作品中这些无所不在的武汉口头语言烘托出了历史中的武汉都市日常生活氛围。如,在叙述楚生的童年生活时,叙述了从民生路到集家嘴一带武汉青少年与长江与码头有关的日常生活;通过汉梅与楚生青梅竹马的交往,穿插讲述了武汉夏天乘凉的竹床阵、普通市民有滋有味的精致晚餐、弄堂飘出的楚剧演唱,以及海员俱乐部附近以草帮侧巷为代表的里弄生活风情。在写伟胜与琴琴约会的同时,描述了租界内与租界外街道居民阶层的区别,以及鄱阳街江汉村的住房特点。通过对文革时期从黄陂街到三民路的批斗场面的介绍,侧面呈现特殊时期武汉都市生活;在叙述文革时期武汉社会治安状况的同时,介绍了六渡桥、公安街、五马路三条以“破脑壳”出名的街道……在这些武汉都市日常生活的叙述中,凸显了武汉的城市性格,泼辣、豪爽、精明、不屈,总之,鲍红志的叙述来自他的生命,是这座城市雕塑了他的人生,他是在记录这座城市的自我讲述。
当然,更重要的是,《楚生》在文学上第一次塑造了一个楚剧艺术家的形象。小说通过楚生的成长,楚生与汉梅、琴琴、菊菊三位女性的爱情、婚姻,楚生与老戏骨、琴师的师徒交往;老戏骨、琴师与徐妈的暧昧历史,较丰满刻画了几代楚剧艺术工作者对艺术的热爱以及付出的代价,当然这种代价不仅仅是楚剧艺术工作者自身物质生活窘迫、价值尊严受到的屈辱、情感生活的坎坷,更有中国历史和社会风云的波澜、诡谲、苦难。文革对文化、文化人的冲击,市场经济对戏剧艺术的考验,文化管理体制对艺术的制约,信息时代文化传播方式的繁多与大众文化消费的乱象……楚剧人的人生与中国社会历史的交相纠葛,有力地说明了楚剧艺术的历史和命运不仅仅是一个剧种的历史和命运,而是历史和文明发展的折射,是历史的理性与非理性矛盾冲突的影像。
《楚生》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叙述,多层次的内涵和丰富的意蕴,几代楚剧艺术家的人生命运,让武汉近百年的城市历史和社会风情丰满多姿、魅力四射。在传统戏曲艺术深受市场冲击的当下,《楚生》所揭示的几代艺术家积淀的楚剧精神或许更应引起我们关注和思考。
 本文来源:荆楚网-湖北日报
本文来源:荆楚网-湖北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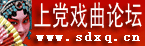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5/3/22 20:03:24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15/3/22 20:03:24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