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网友邢济霖提供该资料)
作者:王冠亚
我养兰花只是为了传送信息,因为凤英的生日和忌辰都在兰花飘香的季节,她和春是同来同往的。我家还保留着凤英的生活习惯,除了逢年过节按照凤英老家桐城罗家岭的乡风吃面条外,都爱吃大米。然而为了凤英的生日吃面条,孩子们也是绝对拥护的。有什么口角纠纷、思想矛盾在这日子里也最容易解决。这两天才是我们家真正的春之节。
今年这天,我更喝了两杯酒,立即仿佛腾云驾雾,浮想联翩,我顿觉年轻多了,竟动了“寻芳”的雅兴,飘飘荡荡来到了护城河畔,槐花从中。突然,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林间,好生眼熟。我不避瓜田李下,径直走上前去,她也绝不躲闪。朦胧的身影一下廓清——天啦!她就是凤英!还是当年那样年轻,还是那双火热的眸子!
“你!你还活着——”我不愿说出那个我不愿说的字眼。
“你能把我和死联系在一起吗?那是怕连累你和孩子,瞒人耳目的。”
“可是,是我亲手用被子把你包住,用板车拉你,我亲眼看见……”
“你不看见我和睡着的一样吗?你不记得我的脸色……”
“是啊,由于摆脱了烦恼,消除了紧张,她全身松弛,脸色是那样平静,白里竟泛出了红晕,显得那么年轻。
她露出了笑容:“我可记得清,你为我整容,为我梳头,嘴里喃喃不住念叨着‘不会的……不会的……’”她笑得有些美女惨。“后来,你要给我换衣,玉兰、瑞和止住你?”
“那是怕我休克……”
“也是怕你吵醒了我,事情就瞒不下去了!”
“你连我也瞒了!瞒得好苦!十三年了,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
“十三年,好日子才到五年呀!那八年日子——”她沉默了一会。“一个老实女人把我救了,带我东躲西藏。”
“那,你们怎么躲过来的?”我急着问。
“她把我带到她的家乡,一个只见竹丛不见炊烟的深山沟里,讲我是她的姨侄女,来山里养病的,就这样,我隐姓埋名到现在……”
“哦!”我憋得透不过气,半晌说不出话。好一会儿,讲了一句:“只要你活着,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但我不回来了。”
“为什么?”
“山里清静,我已经住惯了。”泪水沿着她白晰的脸庞流了下来,突然问道:“你还能像过去那样帮助我吗?”
我毫不犹豫地说:“你讲吧!”
“我接受了一个新的角色任务。”她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无辜的罪人》里扮演女演员柯鲁齐宁娜。你和我对对台词。”这是她创造角色时的老习惯。
“好的。哪一段?”
“第三幕。你看!”她翻开了剧本。
“啊,那是聂兹那莫夫的台词,不是你的。”
“你念吧!”
“这里没有你的戏。”
“不管它。你念吧!”
我脑子还没转过弯来,随便嘟噜了一下:“谁敢侮辱这个女人,我就消灭他!”
“你这样,激不起我的戏来……”她沉默了。
我带着激动的感情又念了一遍,问她:“你的台词呢?”
她突然从沉默中兴奋起来,用那诚挚而深沉的声调讲着:“我是一个不值一文的戏,来到这世界上好像给人提供一个茶余酒评头论足的材料。我在高贵者面前显得那样渺小,只能在卑贱者中博取一点同情。我活着向往的是安宁。我死了也祈求得到一点安宁……”
“这是柯鲁齐宁娜的台词?”我翻书到处寻找。
“你还记得我的遗书吗?”
“遗书?”我思想简直跟不上她的突变。“记得!记得!”
“人言可畏!”她又提起了这四个字。“英格丽·褒曼最讨厌写自传,可是一天她的儿子讲:‘妈妈,如果你将来死了,人们会根据手中掌握的照片、访问记,以用他们的流言蜚语对你的一生肆意攻击,甚至我们都无法保护你,为你辩护……’她考虑了很久,这是真话。卢梭为自己写《忏悔录》,卓别林为自己写传,我想大抵不在求身后之令名,而在提防人言可畏。阮玲玉不就是这样死的么!在那洛阳纸贵的岁月,好多大字报作家为我写传,叫我至今忧思不解。我是个弱者,不能拿笔写‘自传’了……”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们之间的话从来不需要讲完,甚至不需要说,就会互相明白对方意思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互看眼睛就行。这时,我感到她的心跳了一下,就倏然消逝了。
“你!你!”我拼命向前扑去。然而脚像钉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她却在前面朝我微笑。我挣扎着,终于醒了,墙上凤英的照片,闪动着那双火热的眸子朝我笑着。
我沉思了好久,拿起笔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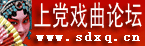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1/9/28 19:56:5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1/9/28 19:56:53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