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林 荣
台上笑台下笑台上台下笑惹笑,
看古人看今人看古看今人看人。
——舞台楹联
引 子
不知道现在知道和记住吴婉芝这个名字的人还有多少,如果现在还健在,应该有75岁了。
我与她相识是在1982年,同去忻州参加北路梆子著名表演艺术家贾桂林舞台生涯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我属于忙前跑后的勤杂人员,但我们竟说到了一块儿。
她是属猴的,生于1932年,。我们在一起尽管谈得很多,涉及面也广,但都是愉快的事,我很羡慕她:当一个演员多好啊,天南海北都能去,还能见到中央首长……。
1986年上党戏调演一开始,我们又相遇了。她是评委,我呢?是负责资料工作,同住一个屋。尽管几年不见了,但没一会儿,我又被牢牢地吸到了她的身边。
也许是上了年纪,容易怀旧的缘故,她的话匣一打开,竟倒出那么多的辛酸苦辣。我发现她竟有那样崎岖的经历,每每讲到悲伤之处,她的眼里就含有一种本人浅显的笔墨无法描述的神色,但没有泪。
那么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她都顶住了。
她除了是个名震上党的表演艺术家,还是晋城市第一届的政协委员,同时还是充满爱心且心灵手巧的妻子和母亲。丈夫和儿女们的衣服与鞋几乎全部出自她的双手,那凝聚千针万线的鞋底、祙底,不亚于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有蝴蝶纷飞,有花蕾初绽,特别是枕头上绣的花鸟更是令人叫绝。那随手剪出的窗花,风格粗犷朴实,真是干什么都是把好手。“心灵手巧”送与她可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真正坐下促膝相谈则在1987年,那时因为我在整理《山西省文化志·晋城市群众文化史料集》,里面需要很多的戏剧史料,就和吴婉芝接触多了起来。有一段时间,我经常骑一辆吱吱作响的车子跑到她家,一坐就是一天。有时去了,就见她在和院子里的邻居聊天,总是那么兴致勃勃的样子,脸上的笑容很灿烂。每每看到我进去,就会说,我相好来了,然后拍拍裤子后面的灰,和我往家走,看见我锁车子,就会说,你那车子不锁比锁了还安全,哈哈哈……
在高平方言里,“相好”是朋友的意思。另外“我”、“这”、“那”的读音很怪,和原字发音差别很大,开始听到她说这几个字,就会抿嘴一笑。我发现高平话鼻音还很重,“n”音发不准,会把“粮票”读成“娘票”,每当她喊我名字时,我都不清楚喊的是“林”还是“宁”或者是“明”。
吴的家不大,家俱也不新潮,可见她对家居的要求不是太高,只是卧室很舒适,床上铺的很厚。吴老师(大家都习惯这样叫她)衣着很朴素、头发在脑后随意一夹就出门了,从不刻意打扮,不知道她底细的人,只会认为她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了。她属于长得很俏丽的那种,身材保持得很好。她的性格很爽朗,笑起来总是哈哈哈的,不像有的人会用手捂着嘴、顾做小女人姿态。她的眼睛总是很有神,每当谈到舞台,眼睛就会亮起来,面部表情特别丰富,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来上一段。我就是在她的家听到了《皮秀英打虎》里的无伴奏唱段的。
岁月真是无情的手。不论你是否曾经美丽还是丑陋,也不管你有过多少荣耀和多么平淡,都会让你在岁月的消磨中把曾经浮躁的心归于平静,都会在你心上和身上刻下深深的不可磨灭的痕迹。
她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照片,我看到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两条粗粗的辫子,眼睛大而有神,表情很羞涩,但极为清纯,照现在年轻人的用语——很阳光而不做作。还有很多的剧照,尽管是黑白的,但仍然可以看到她风华正茂的英姿。看到那些照片,我始终无法把《三关排宴》(上党戏曲片)中的威严端庄、雍容华贵的肖银宗与眼前普普通通的她重叠,也无法把她年轻时的戏曲录音中的甜美唱段与现在沙哑的声音合在一起。
厚重油彩的遮盖会让人更美丽,但素面演唱时,更能让演员的表情牵着你的思绪。每当讲到那些伤感的地方,她的眼光会暗淡下来,但很快又恢复了。有的时候,谈着谈着,她会突然陷入沉思,眼睛会迷离起来,尽管面对着你,但眼神似乎会穿越你的身体,看到很远的过去。丝丝烟缕会在她的手里弯弯曲曲的自然升腾着。这个时候,我总是静静的打量着她,不轻易移动身体,也不发话询问,生怕打断她的思绪,任由时间在滴答中悠悠的走着,任由她在旧日的时光里漫游着。
她抽烟很厉害,把烟放在嘴上时,总是深深的吸一口,眼睛会眯起来,你会看到烟灰一下子多了一截。她习惯用大姆指、二三姆指共同负担烟的重量,而不像别的男同志,把烟夹在手指缝里,所以,她的三个手指都是黄黄的。
吴婉芝的谈吐极为幽默,妙语连珠,听起她聊天南海北来,不亚于看一本好的小说。她的声音哑哑的,很有磁性,语速极快,用高平方言诉说起来,很有意思。她的语言应该用“诙谐、幽默”来作定语了,时间会在谈笑中匆匆流走。客厅的茶几上总是放着一个玻璃罐头,里面放半截水,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盛烟灰的罐头瓶推到她拿烟的手下,让烟灰自己落入……,每当烟头扔进去时,都会发出“嗞”的一声,然后悄没声息。
她说,我不喜欢烟灰。
她的谈话一直继续着,记忆力特别好,一些陈年往事在她的叙述里都会动起来,说着说着,她会告诉我,这些只听不要记,清楚吗?嗯,我会立刻点点头,不记。
她很少说到孩子,总是匆匆带过,但仍可以从只言片语中感到她对子女的那份牵挂。我一直觉得她有着一般女人所没有的忍耐力及刚强,柔弱的肩头扛着比一般人多得多的份量,也许这就是名人之累吧。
她的艺术造诣是有目共睹的,是上党戏剧最著名的戏剧家。但人有在台上的风光,就有在幕后的寂寞,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就在她的叙述中与往日的灿烂人生连起来,串成了她完整的人生。
我和她说过几次,希望她能把自己的经历记下来。她也曾说,有许多人都着手给她整理,但都没有结果。我深知自己的文笔抬不到桌面,不敢揽活。我回去后有意识地回忆了她的讲述,发现不用别人铺排,仅她的叙述则可成文,但又没有十分把握。
于是,我边回忆边写着,下面的文字就出来了,我起的作用只是将她乱七八糟的讲述理顺成章,加了一些合理修饰与连接词及标点符号。
前一百页送去了,我等待着“结果”。几天后,我去了她家,她说这几天睡不着觉,吃安定也无济于事,头天看了一半就哭得看不下去了,如烟往事如放电影似地又到脑子里走了一遭,以后两天,边看边哭。我深知自己的文笔不会如此感人,只是触动了她某段伤心记忆神经,才引发了“黄河决口”。
终于,她认可了。她说,很想印成铅字。但后来告诉我,一直没找到愿意出钱的,尽管现在看来就几千块钱,但在那时,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何况,她已经很久不演戏了。
人大致分有三种,一种是什么情况下都宁折不弯,一种是什么情况下都是宁弯不折,大多数人属于中间的。能直则直,需弯则弯。尽管需要弯而直者,长折腰者不在少数。我觉得吴婉芝是属于前者,认准目标一直往前,这性格成就了她的演艺事业,执著使之攀登上了上党戏剧高峰;这性格也造就了其生活悲剧,而且很惨……
我曾试着想过她的另一种活法:放弃她的爱人,选择另一个可以让她暂时过上安逸生活的人,那她会幸福吗?不过,如果她能选择别的人,那一定不是吴婉芝了。
婉芝有婉芝的生活,是唯一的。
现在就让我们随着婉芝的思绪,走进那已经流失的岁月,去感受那里的风吹雨淋,去触摸那些我们曾经熟悉和陌生的一草一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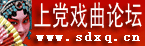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2/1/9 20:28:28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12/1/9 20:28:28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2/1/9 20:33:14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12/1/9 20:33:14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2/1/9 20:33:56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12/1/9 20:33:56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2/1/9 20:37:19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12/1/9 20:37:19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2/1/9 20:38:47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12/1/9 20:38:47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2/1/9 20:39:34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12/1/9 20:39:34 [显示全部帖子]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2/1/9 20:40:25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12/1/9 20:40:25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