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网友晴耕雨读发的一个帖子,很喜欢,转在这里。
老舍之子谈老舍与赵树理的友谊
文·图◎本刊记者 彭斐
老舍与赵树理,是现代中国文坛上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文学大家,一个是京味,一个是乡土味;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乡村学究;一个是留美留英的洋学士,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土作家。但他们的作品艺术价值是相同的,他们的人格风骨是相同的,他们不因艺术上的差异而文人相轻,也不因成就上的高低而互相倾轧,而是在风和日丽时携手同庆,在风狂雨骤时互相扶持……
来自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曲艺代表
谈到老舍和赵树理,老舍的儿子舒乙立即来了精神,“老舍和赵树理是在解放后认识的。1949年4月,赵树理是跟着部队由解放区来北京的,老舍先生是1949年底由美国回来的。”
介绍他们两个人认识的人叫凤子,凤子当时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女演员。凤子当时在家里宴请宾客,他们二位都参加了,于是就结识了。“那时候我不在北京,我估计这个时间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的时候。”舒乙说。
1950年5月30号,北京市文联召开了成立大会,这也是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大会上,老舍先生被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李伯钊、赵树理、梅兰芳等为副主席。
“这个时候老舍和赵树理就是同事了,而且是最核心的同事。”舒乙说,“当时赵树理的住处就在他们办公室楼上。”
当时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说说唱唱》,这是一个民间文学的杂志。杂志刚刚成立时,主编是赵树理,“老舍先生来了以后,老舍成了主编,赵树理变成了副主编,但实际上还是赵树理在负责,老舍就等于在里面挂了一个名。因为他是文联主席,平时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舒乙回忆说。
老舍的一生大部分都生活在国统区的城市,而赵树理则在条件艰苦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过着农村的生活,但两人为什么会成为莫逆之交?
“老舍和赵树理有绝对共同的爱好,就是民间文学,即使在创作研究侧重方面也完全一样,所以后来他们两人成为莫逆之交。”舒乙肯定的说,“虽然两个人并没有在一起共同创作过作品,即使赵树理在创作上更侧重于描写农民的生活,而老舍先生更侧重于市民生活描写,但他们在民间文学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描写的人民大众,他们的眼睛看的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官员,不是富人,而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普通老百姓的构成就是大量农民和城市无产者,所以基于这一点来说,两个人是完全一致的。”
老舍和赵树理都特别爱好曲艺。舒乙认为,曲艺也可以看作是他俩的共同语言。《说说唱唱》上刊发的大都是曲艺类作品。
舒乙说:“在当时的曲艺方面,中国的作家是根本不行的。当时中国的作家大都是洋作家,是留学归国的学生,对曲艺是一门不通。”
根植于民间艺术的曲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多数时间都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就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作家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学生和留洋回来的,实际一点曲艺都没有接触过,既不会,同时又很讨厌这个东西。像打鼓、相声、单弦、快板、山东快书、河南坠子这些艺术,不仅不会,而且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一层的人,没有最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所以也根本不会去听,他们都高高在上。在民间戏曲创作上,五六十年代的那一批老作家,除了老舍和赵树理,任何人都不会。这么多作家中就只有两个人,又懂曲艺,又写曲艺,又喜欢曲艺,一个来自解放区、一个来自国统区的两大人物就是当时曲艺的代表。”
曲艺先驱的莫逆之交
虽然老舍和赵树理没有在一起演出过,但老舍先生却经常会在家里组织聚会,聚会的时候他们二人会自告奋勇地演很多东西。“赵树理是一个又说又闹的人,上党梆子经常随口就出来了,高声在屋里吼。”舒乙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脸上时不时出现会心的笑容。
回到北京以后,老舍有了自己的小院子,他常常把小饭馆的菜叫到家里来。有一次,菊花盛开,他特意请了赵树理、欧阳予倩等好友来赏花。饭后,桌子一撤,余兴开始,老舍打头,先来一段京戏《秦琼卖马》。赵树理站在屋子中间,仰天高歌,唱的是上党梆子。
“老舍先生会很多东西,他是一个特别幽默,活泼、热情的人,这种场合的话,少不了他们两个当主角,其他的人都不会,也只有看的份。上党梆子那种东西是需要吼的,而赵树理就是那种会吼的人,特别高亢。”
“我在家看他表演是经常的事,他就喜欢这种东西。作为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对梆子那是热爱的不得了,赵树理是张嘴就来,而且他唱的梆子特别的滑稽,能把人乐过气去,比如‘早上出得门来,屁股朝前,肚子朝后。’都是特别滑稽的一些东西,能把人肚皮笑疼了。”舒乙说。
老舍对赵树理的作品也是喜欢的,老舍很少写评论,但有一篇评论是写给赵树理的。他在看到赵树理新作短篇《套不住的手》后,“满心欢喜”,专门写了一篇评论。他在评论中说:“我也曾写过一些篇小说,都不怎么出色。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我总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儿。”他赞扬赵树理“他的文字是多么从容而又严整呵!他好像一点力气也没费,事实上却是字斟句酌,没有轻易放过一个字去。”他又说:“从字里行间,我还能看到他的微笑,那个最亲切的微笑。”可见他对赵树理的感情之真挚,性格之熟悉。他们之间是真正的志同道合,亲密无间。
赵树理对老舍的作品也很关注。老舍的剧本《方珍珠》上演前就让赵看过。赵树理在《方珍珠》剧本读后感中说:“这剧本刚刚脱稿之后,我已得到先睹之快。”他在文中对这个剧本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了精辟的分析。
老舍和赵树理都是写戏的。老舍先生写了一个戏叫《柳树井》,赵树理写了一个戏叫《罗汉钱》,都是解放初的戏,而且都是宣传《婚姻法》的。《婚姻法》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大法,当时要解放妇女,要反对包办婚姻。他们二人一个人写了一部小戏,后来都演出。
“有一次看《罗汉钱》演出,我们坐在一起,我就非常注意看赵树理的表情。当时的椅子后面都有一个小平盘,前面人坐着,后面的人可以喝茶。赵树理的手就放在前面的小平盘上,随着戏开演,赵树理很快就入戏了,把小平盘当作鼓敲了起来,而且表情是得意万分。所以说他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他表现出来的就是很自然的喜欢戏曲。”舒乙回忆说。
“他当时打鼓的状态和形象,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民间曲艺的这一套东西赵树理特别棒。”舒乙说,“民间的曲艺,民间的戏曲,民间的乐器,他都是拿得起来的,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在动作与语言的运用方面,在赵树理那里已经达到了极致。“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编的,反正是他张口就来。但我估计这不是他自己编的,而是真正的民间的才有的那种滑稽的东西。”
“老舍也特别喜欢这些,所以他们两个谈得来,他们两个是好朋友,这绝对是有原因的。”
“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文学成就,这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有定论的。但是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他们是现代曲艺改革的先锋。现代曲艺要改革、要改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他们是现代曲艺改良的先驱,全国就这么两个人。既是杰出的贡献,又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特点。这是别的任何作家都没有的。”舒乙总结说。
不熟悉城市生活的农村作家
进城以后的赵树理,并没有因为生活环境的差异和北京土生土长的作家格格不入,但赵树理一直保持着农民的那一套生活方式。
“解放后解放区的作家是主人公,而赵树理是解放区最有名的一个作家,所以别人也不可能排斥他。”舒乙说。“但城市生活对赵树理来说,完全是陌生的,所以也闹了很多笑话。”
至今赵树理喝酒的一段往事仍清晰的记在舒乙的脑海中。赵树理从老舍家回文联的住所,要穿过整个王府井,比如说当时王府井有三家小酒铺,赵树理每一家都得进去喝一杯。
“喝一杯是怎么个喝法呢,进去把钱往柜台上一放,然后由酒坛子拿‘提溜’倒一杯,仰脖而尽,不是慢慢的喝,碰到第二家再来一下,第三家也是如此,把所有酒铺喝个遍,赵树理这才会回去。”舒乙说,“旧社会的时候,一般乡下赶马车的都这么喝酒。进去把钱拍到柜台上,就去喝一杯,而这时马车还在继续走,车夫要追着马车走,所以赵树理这是赶马车人的习惯。但是赵树理每一家都要进去,只要有八家他会喝八杯,五家五杯,三家三杯,而且不要下酒菜。”
“在北京,赵树理一直是这个习惯,所以大家看着特别可乐。在朋友家里,赵树理一喝酒就闹,开始唱,开始跳,开始耍。老舍也挺能喝酒的,而且他和赵树理在喝酒的时候肯定是要划拳的。”
赵树理还有一个习惯,睡不惯席梦思。“比如说出国,作为领导的赵树理肯定会被上级派去出国,他就会等到很晚很晚,人都散了的时候,服务员也休息去了,赵树理就偷偷的在地板上睡,因为他睡不惯席梦思,第二天大清早他就起来,把被窝放到床上去,把房间搞好,怕别人看见笑话他。”
赵树理就是这种习惯,他绝对睡不惯软床,一直保持着在抗日根据地时,和当地农民一起生活的习惯和作风。
“他有很多很多笑话,就是那种农民似的笑话。太行山区哪有席梦思,就连木板床都没有,都是很硬的土炕。”进北京后,赵树理就住在北京市文联,而且睡的一直是木板床。
上世纪90年代,舒乙在筹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时,做过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的时候,要做一尊赵树理全身的雕像放在院子里。雕像一共十几个人,作为解放区出来的作家就是赵树理。负责的雕刻家是中央美院的雕刻学的教授孙家钵。他就问我怎么雕,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赵树理在前面走,后面牵一头驴,驴上坐一个乡间的小姑娘,小姑娘的原型就是《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孙家钵一听就来劲了,说这个东西肯定特棒。”
雕刻过程中,孙家钵问舒乙,“赵树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舒乙说:“第一,他是一个驴脸,极其丑陋,水蛇腰,有点驼背;穿一套窝窝囊囊的中山装,口袋里别一支钢笔,兜里面鼓鼓囊囊的放半块窝头,背着手走路,穿布鞋。”
后来雕刻真的按照舒乙的描述一样,铜质雕像,驴上面坐着一个梳大辫子的乡下小姑娘,放在文学馆的院子里,舒乙和孙家钵都很得意,因为这完全是一个艺术品,但是舒乙就怕赵树理的家属不同意。
“哪知道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从报道上看到雕像的信息后,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不可以翻一个你这个雕像,我问干什么,他说放在他们家乡的街心公园的中心位置。当时我就知道这完全得到了赵树理家属的认可,赵二湖完全认为这是一个神似的东西。”舒乙说。
“但赵二湖的想法后来并没有成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搞成,现在搞了一个标准像,比文学馆的那个要坏一万倍,特别不像赵树理,特别丑陋。当然这个丑陋是从雕刻的角度。”舒乙遗憾的说。
用友谊写下的文人的高贵品质
到北京以后,赵树理的作品不是太多,并且经常受到批评。他很苦恼。他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山西,生活在他熟悉的环境里。北京对他来说太陌生了,所以进城以后,他在创作资源上有点枯竭,所以他频频表达了回山西的意愿。
对赵树理的创作,社会是承认的,他的作品雅俗共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实际上在文坛上赵树理始终不被承认。那些知识阶层认为他的作品是下里巴人,不屑一顾。甚至现在人们排定“大师”座次,他也名落孙山。
其实在建国之初,就有这种情况。赵树理从山沟沟住进了北京的胡同,表面上成了精神贵族阶层的一员,实际上却格格不入。当时的文艺界被人们称为“酱缸”,置身其中是无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
上世纪50年代初的赵树理,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但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赵树理在作协没有官职,他又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
“解放后的文学理论是非常左的,赵树理有比较高的文学修养,别看他生活的样子像个老农民,但他中西的理论都非常好,各种名著他都看过,他自己有一套文学标准。他经常是离经叛道,离开极左的地方,这一做法在当时是要受到批判的。”舒乙说。
“比如说赵树理描写一个正面人物,这正面人物有很多缺点、毛病,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以的。正面人物就是要高、大、全,没有任何缺点,不会谈恋爱,什么都没有,是一种空中楼阁似的高大形象。但赵树理绝不会这样去描写,他肯定会描写一个有声有色的活灵灵的人,这个人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缺点,有自己的毛病,是一个活人,这种做法绝对会受到批判。”
“赵树理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作家,对于政治环境他是不会回避的。”
当赵树理遇到批评时也会找包括老舍在内的朋友进行交流,但他也要写检讨,以寻求过关,这对于赵树理来说是相当苦闷的。
“赵树理解放以后就不快活,一些自己的想法、真心话也只能在私底下和朋友们交流。”舒乙说,“赵树理是一个有见解的人,包括对时局的见解,像他这种智商很高的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这样,在时局和他的作品之间肯定会有矛盾的。其他人不会因为他地位高,特别有名,就放过他。”
“1956年,赵树理在山西待了半年以后,如实的反映了当地农村的状况。这在当时大跃进风潮下,正赶上反右倾扩大化的时候,是绝对不可以的。1956年是赵树理建国后思想和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开始以文学的或非文学的方式向执政者们‘进言’。”舒乙说,“赵树理日子不好过,对于儿女的生活他不太管,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不让他们有特权,他始终过着一种特别低调的生活。”
1965年,赵树理真的就回山西了,但一回去就倒霉了,文革的时候,赵树理的遭遇很惨。
在文革中,老舍宁可自沉于太平湖以死抗争,也不愿向丑类低下高贵的头;而赵树理在被关押到山西省高级法院里后,仍对看望他的女儿说:“近年来我几乎没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
赵树理的性格决定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但不要说赵树理,当时任何人到那去都会是这个下场,当时完全是一个疯狂的状态。
老舍选择了自杀,而赵树理最后被整死了。老舍与赵树理,用生命捍卫了作家的尊严,用勤奋铸造了文学的辉煌,也用友谊写下了前辈文人的高尚品质,与而今忙着打文坛官司的文人,以笔战互相攻讦的新秀们与之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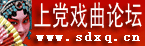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1/4/1 18:44:0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1/4/1 18:44:03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1/4/1 18:4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1/4/1 18:4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1/4/1 18:54:5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1/4/1 18:54:56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1/4/2 19:34:3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1/4/2 19:34:39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