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比较成熟的、经典的中国戏曲也有这样的倾向。比如,叙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有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的《长恨歌》、白朴的《梧桐雨》及洪昇的《长生殿》,情节故事基本出入不大,但是表现的情感却有很大的出入。《长恨歌》是诗歌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作品,是一部长篇叙事诗。从杨玉环入宫受宠到渔阳兵变、贵妃缢死,从避祸幸蜀到回銮京师、睹物思人,从上天入地的寻觅到天堂团圆,娓娓道来,迂徐曲折,是《梧桐雨》和《长生殿》故事之所本。戏曲《梧桐雨》中可以明显看到《长恨歌》的影响,作品第四折的强烈抒情和伤感色彩正是《长恨歌》诗后半部马嵬兵变后玄宗见山川景物触目伤情部分的强化和扩大,具有很强的“剧诗”属性,整整一折几乎是唐明皇一个人在抒怀,表现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叙述者抒情转化为角色抒情。而且《梧桐雨》中代言体形式与诗歌相结合的模式,为诗歌意境转化为戏剧意境创造了条件。《长生殿》就爱情的呈现方式和展开过程言,可以大致分成纵情和情悔两大阶段。前22出仍脱不出帝妃情事的描写范围,为纵情阶段;在25出之后则与此前同题材作品大有不同。作为一代帝王的李隆基在25出以后一直处在追忆、悔懊、痛苦之中,其中包括了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绵延怀念(见于《闻铃》、《悔情》、《见月》、《改葬》、《雨梦》等出),也有杨玉环对李隆基的思恋(见于《冥追》、《尸解》、《仙忆》、《补恨》、《寄情》等出)。文本中通过大量的唱、白、介,将两人在明冥两界的情思表现出来,这是主人公的深情独白,也是明冥两界的深情对话。其间有大段的曲词,美伦美奂,很好的表现了人物的生死深情。
徐麟《长生殿序》曰:《长生殿》“尽删太真秽事”,“或用虑笔,或用反笔,或用侧笔、闲笔,错落出之,以写两人生死深情各尽其致。”[7]金圣叹在言及《史记》和《水浒》的区别时说,《史记》“以文运事”,而《水浒》“因文生事”,明确地表达出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关系。洪昇的《长生殿》之于历史,可以叫做“因情运事”,作者以一己之心,去构建史事的情感氛围,在简约勾勒的历史进程中增添、营构出富蕴诗意的情感氛围和多情画面,借史融情。正如剧中人物李龟年一段曲词所言,“[转调货郎儿]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历史成了“传幽怨”、“写烦愁”的背景和凭借,历史的冲突淡出,而个人的情感冲突得以凸显。作者这里用“拨繁弦”、“翻别调”的诗性的、诗艺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叙事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张力关系,抒情性和叙事性之间得到了有机的融合,是“戏”与“曲”二重性处理的典范。时人将它与《牡丹亭》相提并论,确实是有道理的。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出死入生的离奇情节著称,但是这情节所遵循的,仍然是情感的逻辑:“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澜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惊梦》)……由于是沿着情感的线索发展,而不是遵循逻辑的公式进行,全剧的结构就成了一种抒情诗的结构。《牡丹亭》属于浪漫主义的表现性的文学作品,与历史剧的现实主义品质不属同一层面,而古人把它与《桃花扇》并提,足以说明当时人对戏曲尤其是历史剧性质的体认。
中国戏曲虽然注重讲故事,并不只是为了讲故事,其创作的追求是写好曲子,即对题材、故事进行诗化处理。戏中的主人公与其说是叙事主人公倒不如说是抒情主人公;而大众对戏曲的欣赏,也往往是在熟知的故事的基础上直接进入人物,主要欣赏戏曲对情的演绎。陈世骧先生在《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指出:“中国所有的文学传统统统是抒情的传统。中国戏曲却在叙事架构之上,展现了抒情精神。”可见在现代观念中被认为是叙事体的戏剧,在中国文化、文学强大的背景下成为抒情性很强的叙事艺术,甚至可以看作是抒情艺术。尽管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都把突破窠臼、翻新出奇作为戏曲创作构思的主导,比如李渔《闲情偶寄·结构第一·脱窠臼》就主张:“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孔尚任《桃花扇·小识》亦云:“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但仅从上面表中比较的情形来看,中国戏曲在情节方面的创新还是有限的。然而,对于中国戏曲的传奇性亦即情节性而言,传奇性的本质意义是对人之常情的夸张、强调并使之在常情的基础上升华成为奇情。在这中间,情是原则也是动力,只有以情为动力和起点张开想象的翅膀,才能结构出奇特美好的戏曲情节。
从《长恨歌》到《梧桐雨》可以看到叙事者身影的淡化和剧中人形象的突出,这是体裁变化使然;同时也可以看到诗性传统的绵延,这是戏曲对诗体的承继。其间可以发现诗性的淡化和戏剧性的增强,这是戏剧本身成熟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戏曲诗性发展的痕迹,可以看到抒情性与叙事性的离合与位移,时而抒情性强于叙事性,时而叙事性胜于抒情性。今天的中国戏曲,抒情性与叙事性有机的契合、融合状态,确实是经过长期艺术选择而形成的独特的不可移易的审美状态,也是最佳的审美状态。
中国戏曲是“叙物以言情”的诗,总体而言,它表现出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特点。作为中国重要的叙事艺术形式,重视情感的抒写,在叙事中追求诗意,也的确是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表征。戏曲以宾白叙事,通过叙事引出曲文,用曲文抒写人物的内心情感,这也就是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所说的“以曲打科,以白引曲”,它很好地处理了诗、歌、舞之间的关系,让叙事、抒情、舞蹈、音乐等因素在戏曲的名目下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对应与互补的有机整合体。从理论上讲,中国戏曲形成这一特征经历了漫长时间的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与整合,经由元代至明代中叶的曲论(注重音律与文辞)再到明末向“文”(注重叙事性)、“剧”(注重综合性、剧场性)观念转移,直到清代“曲”、“剧”、“文”并存和包融,最终熔炼、凝合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这一艺术形态由于很好地解决了抒情性与叙事性的张力关系而充满着诗性,故而有“诗剧”或“剧诗”之称。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戏曲的艺术是融合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而加之新组织,他是文艺中最高的制作,也是最难的制作。”[8]
传统戏曲“剧”与“曲”的完美融合而形成诗剧特质使得戏曲在世界戏剧体系中独树一帜,成了世界上独特的表演体系,其中也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戏剧艺术的独特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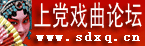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1/7/17 17:03:0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1/7/17 17:03:07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1/7/17 17:05:3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1/7/17 17:05:32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1/7/18 9:47:5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1/7/18 9:47:59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怦燃心动
怦燃心动
 Post By:2011/7/18 20:29:1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1/7/18 20:29:16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1/7/18 20:39:3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1/7/18 20:39:36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1/7/18 20:42:0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1/7/18 20:42:02 [只看该作者]

